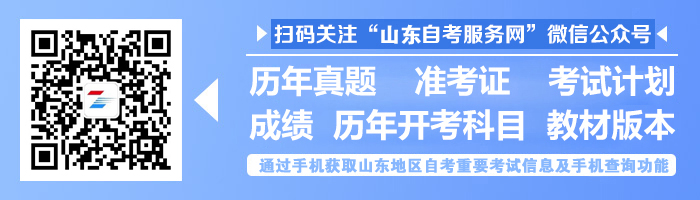唐末长安民俗生活论
《北里志》是一部描写唐代乾符年间( 875-879)长安士子狭邪生活的实录式笔记小说,写成于唐代中和四年(884)前后,作者孙棨。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少数内容也表达了歌妓们的生活和对爱情的追求,并保存了士人和歌妓的一部分诗歌作品,故其对研究唐代风俗民情和唐末诗坛与士风都有重要意义。
一、科举宴会
唐代科举文化考试科目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又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重帖经、墨义,死记硬背即可;进士科重诗赋,则需要相当的才华。而且,明经科每年录取名额是进士科的几倍乃至十倍,正如清赵翼《陔余丛考·进士》所说:“唐制有与后世不同者,后世三岁一会试,唐则每岁皆试;后世放进士多至三四百人,少亦百余人,唐则每岁放进士,不过三四十人……宋初犹每岁一试,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今问岁一科举。英宗二年,又定令三岁一科,此后世三年一乡会之始也。”至于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考试的科目,日期和内容一般临时决定,是朝廷选拔突出人才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进士科遂成为唐代士子的最高目标,故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义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虽然,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制科》亦云:“御史张璟兄弟八人,其七人皆进士(科)出身,一人制科擢北,亲故@@@@,兄弟连榻,今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篇》也说:“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彰于武德而甲于贞观。盖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赞神圣,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回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进士及第后,一连串的曲江宴、杏园宴、雁塔题名等庆祝活动推波助澜,使进士不仅成为才华、尊贵和荣耀的象征,而且成为世人谈论的焦点,更是当世所有女性仰慕的对象。《北里志》正反映出唐末进士及第后的盛大庆祝活动。
首先,是杏园探花宴。据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唐时新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为探花宴,以进士少俊者二人为探花使,人园折花,故名探花,或称探花郎。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尽了及第者的喜悦和得意。晚唐以来,风俗侈靡,游宴更甚,故孙棨云:“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
其次,是曲江宴。曲江为唐代京都长安东南的游赏胜地,春榜进士与朝廷官员常于此举行庆宴,称为“曲江宴”或“曲江会”。唐韩鄂《岁华纪丽·春》曰:“春放榜,进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云:“咸通十四年,韦昭范先辈登第,昭范乃度支侍郎杨严懿亲……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帐之盛,罕有伦比。”这种聚会,往往有歌妓参加。如《北里志》“牙娘”条云:“故硖州夏侯表中,相国少子,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闻者,宴集尤盛。”也正是在乾符二年(875)春天的曲江宴上,孙棨见到平康北曲素无名声的小家歌妓刘泰娘:“乱离之春,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侧下车而行,年齿甚妙,粗有容色。”孙棨当晚便寻访刘泰娘,并题诗其舍:“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刘泰娘因孙棨的抬举而声名大振:“同游人闻知,诘朝诣之者,结驷於门也。”
再次,是雁塔题名。唐代新进士及第,赐宴后,有前往慈恩寺,在大雁塔下题写自己姓名与诗的风尚。后因称考中进士为“雁塔题名”。会昌年间,曾为宰相李德裕禁止,后恢复。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记云:“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时白乐天二十七。”又“进士题名,自神龙(唐中宗年号)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会昌三年,赞皇公(指李德裕)为上相……于是向之题名,各皆削法,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在上述一系列宴会后,新进士还要邀请同僚设家宴庆贺。《北里志》记载尚书杨汝士之子杨知温及第后,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这些宴会极度奢侈、豪华,往往“水陆之珍,靡不备矣”(《唐摭言》卷三),故孙棨感叹道:“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这股欢乐、侈糜的进士宴饮之风,随着科举考试的进行,一直从岁初延至仲夏。
二、席纠风俗
唐人尚酒,故饮酒习俗应运而生。《北里志》对唐人饮酒多有记载,如尚书胡证与诸力士斗酒时,不但“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而且“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即胡证一人便饮酒一斗左右。正是依赖这种过人的酒量、勇力和气势,胡证制服诸恶人,被群恶呼为“神人”,遂瓦解了一场十分严峻的危机,及时挽救了同年裴度的性命。胡证与裴度,《两唐书》无有传。二人不但是河东老乡,而且都在贞元初擢进士第,故交情甚深。裴度,历任河阴尉、监察御史、河南功曹参军、西川节度府书记、起居舍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胡证,历任太子舍人、户部郎中、御史中丞、谏议大夫。元和九年(814)党项屡扰边时,胡以“儒而勇”选拜振武军节度使。而郑光业新及第宴请同年时,有一名歌妓患心痛病猝死在宴席上,同年皆惶骇,郑光业却若无其事,撤筵中器物,悉授其假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平康名妓颜令宾卒前,也曾“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就在“离乱前两日(黄巢起义)”,孙棨还曾与进士李文远,乘醉同诣曲中名妓颜令宾。
正是伴随着各种酒宴活动,长安饮妓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中唐以后,奢侈之风在社会上盛行,故《唐国史补》卷下记载道,“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旧唐书穆宗纪》云:“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而为乐。”孙棨《北里志》更是感慨道:“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在这种“游宴崇侈”“风俗奢靡”的宴饮活动中,饮妓担任宴饮酒席中举足轻重的律录事。根据历史记载可知,唐朝的酒令行令承继古俗,但组织形式更加完备。参加者人数不拘,一般以20人为一组,每组设一个监令,观察依令行饮的次序。按照当时县令为“明府”的习惯,此人被命名为“明府”(引自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明府之下设二录事:“律录事”和“觥录事”。律录事司掌宣令和行酒,又称“席纠”、“酒纠”。觥录事司掌罚酒,又称“觥使”和“主罚录事”。皇甫孙《醉乡日月》有“明府”、“律录事”、“觥录事”三门,说的就是当时酒筵行令的组织规则。明府管骰子一双、酒杓一只,决定每一项游戏的起结。律录事管旗、筹、纛三器,以旗宣令,以纛指挥饮次,以筹裁示犯令之人;觥录事则执旗,执筹,执纛,执觥,实施罚酒。当时最为人乐道的是律录事(席纠)。他是酒令游戏的具体组织者,是酒筵上的核心人物,故《醉乡日月》说律录事须有“饮材”,即第一要“善令”,熟悉妙令,能够巧宣;第二要“知音”,擅歌舞,能度曲;第三要“大户”,有酒量,能豪饮。
《北里志》便记载了这样一批出色的“席纠”。如歌妓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郑举举“善令章”,“巧谈谑”,故孙偓为状元后,与同年侯潜、杜彦殊、崔昭愿、赵光逢、卢择、李茂勋等数人,多在郑举举处宴饮;俞洛真“时为席纠,颇善章程”。王福娘在上巳日也与其母在曲江“对米盂为纠”。名妓杨莱儿“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与进士赵光远“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爱”。后来,杨莱儿被“阆阅豪家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之后,“人颇思之,不得复睹”。
面对这样一批酒纠身份的聪慧女子,唐代士人抒写了许多美丽的诗篇:郑仁表有赠俞洛真诗,“巧制新章拍指新,金罍巡举助精神。时时欲得横波盻,又怕回筹错指人”,将俞洛真在酒席上的作用、出色表现、神态及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刘郊及第年,郑举举生病,无法参加宴饮活动,遂令同年李深之邀为酒纠,但李深之的席纠能力根本无法和郑举举相提并论,故自嘲曰:“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此外,方干有《赠美人》诗:“酒蕴天然自性灵,人间有艺总关情。剥葱十指转筹疾,舞柳细腰随拍轻。常恐胸前春雪释,惟愁座上庆云生。若教梅尉无仙骨,争得仙娥驻玉京。”黄滔《断酒》诗亦云:“未老先为百病仍,醉杯无计接宾朋。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丝管合时思索马,池塘晴后独留僧。何因浇得离肠烂,南浦东门恨不胜。”诗句中的“簪花录事”,当时便成了“饮妓”或“酒纠”的别名。因此,嗜酒在晚唐是一种社会风气,也是一种生活习俗。
三、国忌行香等习俗
从唐代开始,在本朝帝后及先祖去世之忌日,要罢音乐,停政务,百官行香纪念死者。后来又有百官奉慰、禁刑、断屠宰、不视事等一系列规定。正如《宋史·礼志二六》云:
忌日,唐初始著罢乐,废务及行香、修斋之文。其后又朔望停朝,令天下上州皆准式行香。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亦云:
忌日行香。始于唐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诸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也说:
国忌行香起於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
因此,国忌行香是一种大型的礼佛祈祷活动,是国家级的带有一定政教性质和佛事特点的活动。宋王溥《唐会要·忌日》:“其京城及天下州府诸寺观,国忌行香,一切仍旧。”《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九年》:“勋虽不能用,然国忌犹行香。”胡三省注:“唐自中世以后,每国忌日,令天下州府悉於寺观设斋焚香。开成初,礼部侍郎崔蠡以其事无经,据奏罢之,寻而复旧。’
《北里志》云,“诸妓皆私有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便是国祭行香俗的真实写照——北里诸妓是专门从事娱乐活动的,自然要弄清楚诸帝后忌日,以免犯禁。这足以说明,国忌行香活动已经成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忌行香俗息息相关的,便是宝唐寺讲席活动。宝唐寺原名菩提寺,《隋志》注明其建于隋开皇二年(582),至大中六年(852)改为保唐寺。《北里志》云:“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宋初钱易《南部新书》亦云:“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人道,尽在咸宜。”宝唐寺在平康坊,与诸妓隔街而居。诸妓喜欢去保唐寺,可能与这里讲唱的是尼姑有一定关系,在当时属于俗讲。这些歌妓,每月获准出坊三次,即月之初八、十八、二十八。每次出去,她们还要向假母交纳一缗钱(一千文钱,即银子一两)的保证金。因此,每月之“三八”日,遂成为诸妓固定出坊的日子,也成了士子携妓听讲唱的日子。这三天,京城士子几乎倾城而出,争相期盼一睹歌妓风采。当然,花枝招展的歌妓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京城士子身上。
四、上巳民俗
上已是春季三月上旬的巳日,曹魏以后,这个节日固定在三月三日。这一天,长安市民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最流行的当属祓禊和踏青。
祓禊是一种古老的习俗,一般于春秋两季,至水滨举行祓除不祥的祭礼发习俗。春季常在三月上旬的巳日,并有沐浴、采兰、嬉游、饮酒等活动。《周礼·春官·女巫》:“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熏草药沐浴。”汉应劭《风俗通》云:“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汉张衡《南都赋》亦云:“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引晋王羲之《临河叙》日:“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汉至唐代,赋咏极多,如东汉杜笃《祓禊赋》、晋张协《洛禊赋》、隋卢思道《上巳禊饮诗》、唐沈俭期《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等,皆写此事。
据《北里志》记载,孙棨“春上巳日,因与亲知禊于曲水,闻邻棚丝竹,因而视之,西座一紫衣,东座一缞麻……对米盂为纠,其南二妓,乃宜之与母也。”即孙棨在上巳日与家人在曲江祓禊时,偶然邂逅王福娘与其假母王团儿也陪人在曲江游玩,而此时的王福娘已经被豪主张言买断,孙棨不可复见。
上巳日还有踏青习俗。初春时节,芳草始生,杨柳泛绿,人们至郊外野游,谓之踏青。踏青的日期,因时因地而异,或于二月初二,或于三月上巳,或于清明节前后,晚唐往往在上巳日。如《北里志》之“张住住”条,就间接记载了这一习俗。此条叙述了“少而聪慧,能辨音律”的张住住坚决拒绝富人陈小凤求婚,与童年玩伴庞佛奴智斗陈小凤,最终喜结连理的坊间故事。张住住年将及笄,庞佛奴却“力窘不能致聘”,平康里南富人陈小凤看中张住住,已经向其家“纳薄币”,并约定在三月五日“开元”,即买断张住住的初夜权:
及月初,音耗不通,两相疑恨。佛奴因寒食争毡,故逼其窗以伺之,忽闻住住日:“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庞勋同姓,佣书徐邸,因私呼佛奴为徐州子。日中,盖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当以疾辞彼,即自为计也。”佛奴因求其邻宋妪为之地,妪许之。是日举家踏青去,而妪独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键其门,伺于东墙,闻佛奴语声,遂梯而过。佛奴盛备酒馔,亦延宋妪,因为幔寝,所以遂平生。
上巳日,张住住装病骗过家人,在邻居宋妪的帮助下越墙与庞佛奴幽会,并商定计策。此前,住住家人对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见之”,在上巳日却举家外出踏青,从而让两位年轻人钻了空子。这足以说明,上巳踏青是唐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重要的民俗事项。五、其他习俗
除了科举宴会、席纠、佛教习俗、上巳习俗等重要事项外,晚唐还盛行斗鸡、斗草、打马球、唱挽歌等娱乐活动。
斗鸡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早在春秋时就相当流行。传承至唐代,斗鸡风靡一时。唐玄宗在即位前就十分喜爱斗鸡活动,即位后,玄宗在宫中专门修建了鸡坊(鸡坊在大明宫与兴庆宫之间;斗鸡门在大明宫九仙门外),选养了千余只“金毫铁距、高冠昂尾”的雄鸡,并派五百小儿专门负责训养。上行下效,许多人为此不惜重金,以至倾家荡产。由于斗鸡之风大兴,长安城中男女均事斗鸡,无资购鸡之贫寒者,便玩假鸡为乐。相传唐玄宗在一次出游途中,遇一小儿贾昌玩木鸡。玄宗将小儿召人宫中,使其在鸡坊训养雄鸡。因贾昌训养有方,深得玄宗赏识,遂“金帛之赐,日到其家”。贾昌在当时号称“神鸡童”,社会地位骤变。他的父亲去世时,唐玄宗下令“县令为葬器丧车”:
《城东老父传》:老父姓贾,名昌,生七岁能解鸟语音。玄宗还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训扰(调教)教饲。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运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二。
《新唐书·五行志》: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识者以为鸡酉属,帝生之岁也。斗者,兵象,近鸡祸也。
唐代杜淹在《吟寒食斗鸡应秦王教》中对斗鸡的场面作了淋淳尽致的描写:“寒食东郊道,扬鞴竞出笼。花冠初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功。”韩愈与孟郊的《斗鸡联句》则描绘了斗鸡的场面和斗鸡的雄姿。
《北里志》也记载了这一习俗,亦见张住住条。上巳日发生的事情,张住住家浑然不觉,两天后陈小凤如约前来,庞佛奴利用坊中斗鸡,机智地化解了这一危机:
曲中素有畜斗鸡者,佛奴常与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托宋妪致于住住。既而小凤以为获元,甚喜,又献三缗于张氏,遂往来不绝。
愚笨的陈小凤还以为张住住是处女,故平康轻薄小儿唱歌调侃陈小凤日:“舍下雄鸡伤一德,南头小凤纳三千。”在这一事件中,斗鸡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斗草在晚唐也是较为流行的习俗。斗草,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刘宾客嘉话》云:“唐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白居易《观儿戏》诗云:“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
《北里志》也有对斗草习俗的记叙:年轻的孙棨在长安作举子时,春天随人诣城北平康坊,认识了歌妓王福娘。在众多士人赠诗中,王福娘最欣赏孙棨的才华及诗歌,请孙棨题诗于其窗左红墙,其一曰:
移壁回窗费几朝,指环偷解薄兰椒。
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
由此可见,斗草在年轻女子之间更流行。“无端斗草输邻女”,便是对这一习俗的真实描绘。
此外,便是端午节的打马球游戏。马球是骑在马上,持棍打球之游戏,古称击鞠。唐代长安,不仅有宽大的马球场,而且唐玄宗和唐敬宗等皇帝更是乐此不疲。唐代章怀太子墓出土的《马球图》上,二十多匹骏马飞驰,马尾扎结起来,打球者头戴幞巾,足登长靴,手持球杖逐球相击。这一画面,便是马球场面的真实再现。
《北里志》之张住住条有马球的简略记载:庞佛奴正是在寒食争球时,有意靠近住住的窗下,暗中潜伏,才听到张住住的一席叮咛与嘱托。另外,《北里志》载刘覃进士及第时,“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鄴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慕妓天水仙哥之名,不惜重金召之。”这位年轻的公子,不但是狎妓名角,而且是马球高手。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著录道:
乾符四年(877),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骤驰击拂,风驱电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偔俛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这一记载,无疑让我们对马球游戏有了更直接和形象的认识。
另外,《北里志》还有关于晚唐挽歌习俗的记载。挽歌是古代送葬时所唱哀悼死者的歌,起于汉初田横,后李延年将挽歌分为《薤露》和《蒿里》二曲。《初学记·挽歌》著录有缪袭、陆机、陶潜、李征、卢思道、李百药、上官仪、骆宾王和崔融诸人挽歌诗,多为五言古诗或五言律诗。唐代长安,出现以挽歌为业并享誉一时的现象,时称凶肆。据《北里志》记载,歌妓颜令宾卒后,坊中乐工刘驼驼,从众多士人挽词中选择数篇,制为曲子词,教挽柩前同唱之,声甚悲怆。后来,有四首挽歌流传下来:
其一:昨日寻仙子,辆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竞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
其二:残春扶病饮,此夕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花几日狂。孤鸾徒照镜,独燕懒归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尊一觞。
其三: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骏奔皆露胆,磨至尽齐眉。花坠有开日,月沉无出期。宁言掩丘后,宿草便离离。
其四.奄忽那如此,夭挑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
“自是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歌妓颜令宾的挽歌,逐渐演变为长安城的哀伤,美人凋零与士子心绪在此契合,末世情怀与时代哀音合二为一,最终汇成一滴苍凉的眼泪,悬挂在长安的屋檐下。
总之,孙棨笔下所记的晚唐民俗史料,客观真实,丰富多彩,为后世研究关中等地的古代民俗,特别是长安民俗的变化、演进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http://www.sdzk.sd.cn)
《山东自考网》免责声明:
1、由于各方面情况的调整与变化,本网提供的考试信息仅供参考,考试信息以省考试院及院校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2、本站内容信息均来源网络收集整理,标注来源为其它媒体的稿件转载,免费转载出于非商业性学习目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内容与版权问题等请与本站联系,本站将第一时间尽快处理删除。联系邮箱:8123794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