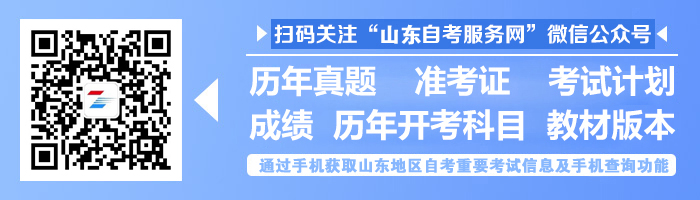我国物权法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 ——关于制定
【编者按】民法典的制定目前已成为最热门的立法话题。新合同法的颁行,意味着制典序幕已拉开,其初步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学者参与立法的热情。在此背景下,关于一国经济体制之基础、确定财产权之归属和变动的物权法自然被提上立法日程:学者起草的两个建议案先后亮相,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征求意见稿也已出台。为此,我们特约请部分专家学者,就物权立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以此为物权立法工作的稳健进行搭建一个对话和讨论的平台,并期望对我国的物权立法有所裨益。
尽管物权法规范有形财产之归属关系,尽管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为有体物,但在物权与债权相对而立的基本财产权体系之中,仍然存在一个“第三者”,这就是无形产权。而无形产权与物权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如果对之不予以适当的分析,则物权本身的地位也许尚难以达到真正的清晰。
众所周知,将财产划分为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为罗马法的传统,但罗马法上的无形财产(无体物)仅指某些财产权利,并不包括近代社会以来才出现的知识产权等。法国民法不仅继承了罗马法的这一传统,而且还扩大了无形财产的范围。在法国法中,无形财产是指不具有物质形态,只能通过思维的、抽象的方式认识其存在的财产,其可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用益权、地役权等他物权以及由《法国民法典》直接加以规定的债权和股权等;二是无形产权。法国法中的无形产权的范围比知识产权的范围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版权以及发明专利、工业设计、商标权等工业产权,而且还包括主体就营业资产、客户、营业所、商业名称以及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商业信息等所享有的权利。
对于无形产权的地位以及将财产分为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这一作法,有些法国学者持否定观点,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有形财产”,因为一切财产都是无形的。他们指出:“物和权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将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类是毫无道理的。从逻辑上讲,不应将物视为财产,因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是物所包含的‘财富’因素而非物本身,物权是权利的标的。无任何人享有权利的物根本就不是财产。”(注:Flour et Aubert,Les obligations,l’acte juridique,A.Colin,8e éd,1991,no.4.)但其他法国学者则认为无形产权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一种现代社会现象,与两类财产的区分并无直接关系。有形财产的概念阐明了所有人对物的直接控制支配的程度高于对无形财产的控制、支配,而无形财产则是一种更为理念化的权利,这种权利更易于自我分解、持续期较短并严格地决定于法律及情势所构成的社会背景。
与此同时,就无形产权是不是一种“所有权”的问题,法国学者也展开过争论。很显然,无形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涉及财产(智力成果及其他利益)和财产的“归属”(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可通过合同而转让(具有可让与性)并具有对抗一切人的绝对效力(为绝对权)。可以说,除了权利客体非为有体物之外,无形产权在许多基本的方面与所有权并无不同。为此,有许多学者认为无形产权实质上就是一种所有权,甚至认为“所有权的‘硬’概念已经被知识产权的‘软’概念所摧毁”。(注:M.A.Hermitte:《非法律技术中的‘软’概念的意义:知识产权的典型》,A.p.d.1985,331et s.)但是,更多的人根据以下理由否认无形产权是一种真正的所有权:(1)无形产权非以有体物为标的;(2)无形产权不能具有所有权的全部权能;(3)所有权一般有永久性,而无形产权通常有时间性(诚然,某些无形产权的时间性形同虚设,如商标权因可无限“续展”其效力而事实上并无时间限制,商业名称也如此,但时间的经过对之仍可发生影响,其表现为这些权利会因停止使用而丧失其效力);(4)法律对于所有权主体之身分一般无特别要求,但无形产权通常须依赖于其持有人的职业与身分;(5)无形产权的存在和实施均须严格依从法律规定。与所有权不同,所有权所包含的对物质资料的垄断利用权(排他性)事实上更带有一种“自然性”,而作为一种法律上的垄断利用权,任何无形产权的产生通常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同时,无形产权中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通常具有国际性,等等。
而在其他国家的学者以及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中,除上述理由之外,经常还被提及的是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问题。如德国著名学者Karl Larenz就指出,精神产品应由知识产权法规范而不由物权法规范,因为精神产品本身虽然表现为物,但其真正价值不一定能够通过其物质载体本身而得以表现,而需要特别的机关依照知识产权法来予以判断。虽然著作权、专利权以及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和保护也须以物权法为基础,但其同时也需要依靠专门的行政法规,而且有时行政法规对知识产权的取得和保护能够发挥较之民法更为重要的作用。(注:转引自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第4页。)
故无形产权为一种“利用垄断权”而非物权之一种,当属无疑。
但是,尽管关于“知识产权是不是一种所有权”的讨论如此形而上,以至于令人怀疑其是否具有实际价值;尽管条分缕析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区别已经被许多人作成了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以至于继续关注这一问题有可能被视为学问上的浅薄,但看起来如此相似的知识产权与物权真的具有本质区别吗?拥有一幢房屋与拥有一项专利,如同购买一幢房屋与购买一项专利一样,当然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为什么合同或者债权制度并不因为技术转让合同的标的与有体物买卖合同的标的不同及由此而导致的诸多“重大区别”而将其拒之于合同法或者债法的门外?学者所揭示出来的物权与知识产权的那些区别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不妨来试试反驳这些看起来很难反驳的理论:
其一,物权必须以有体物为标的,而无形产权非以有体物为标的,故其非物权之一种——这是一项毫无道理、霸气十足的逻辑推理。谁说物权必须以有体物为标的?为什么某些无形财产就不能成为所有权的标的?如果说德国人创设物权体系时根本未考虑到无形财产的归属和支配将成为以后社会最为重大的法律问题,由此而当然地确定了“法律意义上的物仅指有体物”的话,那么,打破或者适当打破德国人在100年前创设的这种完全封闭的物权体制,确定有体物之外的某些无形财产得成为物权之标的,完全有可能正是民法及物权法的一种进步。事实上,“物权之标的仅为有体物”的限制早已被突破。如《瑞士民法典》第137条规定:“性质上可移动的物及法律上可支配的不属于土地的自然力,为动产的标的物。”而《日本民法典》虽明文规定“本法称物者系指有体物”(第85条),但在此原则基础上,该法典实际上承认有不少的例外:如依该法典规定,在债权、股权等权利之上不得成立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但当权利变为证券时,其即被视为动产(第86条第3款);此外,自然力非为有体物,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但是,依日本有关判例,当自然力被置于能够为人力所控制的状态下时,则按物处理(例如,在日本大审法院于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6月29日作出的判决中,“电气”被准用《日本民法典》第173条第1项中的“产物”进行处理)。至于我国民法理论和物权法立法实践,也对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作了扩张的解释:不仅有体物之外的电、热、声、光等自然力应视为物,而且连“空间”也得成为物。(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3页。)既然如此,以无形财产非为有体物来否定其能够成为物权之标的,不足为取。
其二,无形产权不能具有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尤其权利人不能对权利标的实施“占有”,故物权法有关占有的保护以及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等,均不能适用于无形产权。此外,对无形产权的法律救济方法也与物权的保护不同(如对于无形产权的侵犯不可能适用“返还原物”的方法),此条理由殊难成立:所有权为完全物权,所有人得对物为最彻底的支配,但除所有权之外,尚有其他物权,而任何他物权均不具备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其中,抵押权便不具有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能。特别应注意的是,对于无形财产的“占有”虽不能表现为对无形财产的实物控制而是表现为对智力成果或其他无形财产的“专有”(垄断利用),但这种“专有”于无形财产所达之观念控制,与“占有”于有体物所达之物理控制仅有形态上的区别而无本质上的区别,况且传统物权中,对于物的占有非表现为对物的物理控制或者根本不具有对物的实物控制之权能的他物权仍有存在,如地役权、空间利用权、权利质权等。所以,物权法有关占有的保护之规定,应当准用于知识产权等无形产权,如《日本民法典》第205条即规定,对于“精神创造物”,当事人得具有“准占有权”。至于取得时效之能否适用,并非衡量某一权利是否为物权的标志,例如非以占有为要件的抵押权等,不适用取得时效;又如经登记的不动产所有权,不适用取得时效。此外,权利保护方法之差异固然可以反映权利性质之差异,但某些法律救济方法的不同,不等于权利性质必然不同。而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保护方法并非均可普遍适用于一切物权,亦即并非所有权的保护方法均可适用于其他物权。如返还原物之保护方法就不适用于抵押权、地役权等。
其三,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时间性,其产生须法律的特别规定,其保护通常具有国际性,其享有通常与特定人的职业、身分相联系,此外,知识产权涉及更多的行政管理权力的介入,等等;而所有权无地域性且一般具有永久性,所有权没有国际保护问题,法律对所有权主体之身分一般无特别要求。上述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些区别对于揭示二者之本质差异有何意义?就权利设定而言,任何权利的产生均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至于权利设定之程序上的要求,于权利的性质毫无影响。同理,权利效力之存续为阶段性的抑或为永久性的,权利效力之地域范围为有限制的抑或无限制的,均不涉及权利本身的性质如何。
由此,不能不令人思索: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区别究竟是本质的还是非本质的?将规范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之同类性质的关系(归属与支配)的法律截然加以区分,究竟是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还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历史惯性?当对物的占有和控制被认为越来越不重要之时,当“财产”的概念被认为越来越“非物质化”之时,当物权的社会管制被认为越来越强化之时,为什么还要维持以所有权(财产之归属)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物权制度在体系上的所谓“完整性”呢?君不见,由于物权与债权“二分民法财产权制度之天下”的传统,由于作为民法财产权之理论基础之既有的全部知识几乎都是为物权与债权“服务”的,或许再加上某些民法学者对于超出自己理解能力之外的知识产权所自然具有的排斥心理,以及某些知识产权法学者由于对民法基础理论的欠缺而发生的逃离心理,至少在祖国大陆学术界,民法学者和专攻知识产权法的学者之间,基本上难以建立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但凡自称为民法学者的学者,通常以不研究知识产权为特征;而凡自称为知识产权法学者的学者,则大都不会同时认为自己是民法学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完全有可能被放逐于民法之财产法体系之外,不仅压根儿从未实际发生过(为很多学者在其著作中许诺发生的)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三分天下”的盛况,而且连将知识产权究竟置于民法之财产法体系中的何种地位这一问题,也难以达成共识。为此,在讨论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时,过分强调二者的“区别”,不适当地夸张其区别的意义,甚至通过强调知识产权的所谓“人身权属性”以及国家对之进行的较强的行政管理来否定知识产权的财产权性质乃至其“私权”性质,此于民法理论的建设与实践均有害无益。
因此,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无论有理无理,将无形产权纳入物权法体系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必须承认,作为规范无形财产之支配、利用关系的法律,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无形产权法与规范有形财产归属关系的物权法并无本质区别,故无形产权应当作为与物权相关或相联系的一种财产权利而存在,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无形产权应当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对此,德国学者显然表现出一种更为宽阔的胸怀,在德国民法上,虽然法律明文规定“物权的客体仅得为物”,但其理论上存在另一种其层次比物权更高的权利即“对物权”。所谓“对物权”,为特定的人对“广义的物”(包括有体物、无体物以及其他有财产意义的物如著作权的客体“作品”等)的排他的直接支配权。物权仅为“对物权”之一种类型而已,在财产法的其他领域如知识产权领域,也存在各种“对物权”。不仅如此,德国民法学的著述常常有将物权认同于“对物权”的观点,也有许多人把物权法的原理应用于工业产权法的解释和实践,因为“物权和对物权、工业产权确实也有许多相同的性质”。而对于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Karl Larenz尽管有关于“有时行政法规对知识产权的取得和保护能够发挥较之民法更为重要的作用”的观点,但同一学者所讲的另一番话却于我们应当很有启迪。他指出,知识产权与一般的物权相比,个性更为突出,这和它们的标的为精神产品这种无体物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物权法上的物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包括精神产品这种无体物。但是,“因为物权法为一切财产法的基础,故上述规则并不妨碍依据物权法原理对知识产权的拥有和行使的解释,也不妨碍物权保护方法在保护知识产权中的运用。”(注:转引自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第4页。)
总之,在立法体系上,基于破坏在物权与债权区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财产权固有结构的不必要性,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产权不妨以特别法加以规定,但是,在思想观念上,无形产权应当作为与物权法(有形财产权法)相并列的制度与债权法两相对应。同时,物权法的知识和规范在无形产权法研究和立法中的运用,应当成为当代财产法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标签:山东自考 毕业论文 我国物权法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 ——关于制定
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http://www.sdzk.sd.cn)
《山东自考网》免责声明:
1、由于各方面情况的调整与变化,本网提供的考试信息仅供参考,考试信息以省考试院及院校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2、本站内容信息均来源网络收集整理,标注来源为其它媒体的稿件转载,免费转载出于非商业性学习目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内容与版权问题等请与本站联系,本站将第一时间尽快处理删除。联系邮箱:812379481@qq.com。